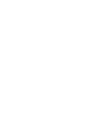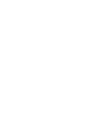【星际np】祈祷落幕时 - 他们的存在主义荒谬当道爱拯救之
夜已经很深了,在这样原始的星球,夜色总是格外浓稠,西奥多看着黑暗像雾气一样弥漫在房间里,里面混杂着忍冬和各类花草的幽香,那一点也不冷冽,还格外的清甜。当月亮从云丛里探出,整个世界又瞬间变得明亮而皎洁,于银色月光的映照下,周围的花香似乎变得更清晰了,丝丝缕缕的,好像要诱导人进入一个仙境。不过,对他而言,这里已经是一个仙境。
她就睡在他的身边,睡的十分恬静。
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西奥多所做的就只是看着她睡觉,看着她的睫毛如何抖动,看着她的嘴唇如何张开又合拢。
西奥多以为只有婴儿才会有这样无忧无虑、毫无警惕的睡眠。
与泰拉统一之战的那段日子相比,在皇宫里充当禁卫的日子已经是十分平淡。而与在皇宫里充当禁卫的那段日子相比,现在于这颗星球上隐居的生活又是更加的平淡。
西奥多终究是一个战士,与利亚姆相比虽然并不显得旺盛,但也追求着战斗的激情,不过于他而言这种激情是可以控制的,更何况在这平淡而渺小的生活里,他觉得自己似乎触摸到了永恒,那永恒就藏在她的身上,叫他更清楚自己是因为她而活。
西奥多很坚定的认为他的生命、他的同僚的生命,包括星际战士及各位统帅的生命,都掌握在她的手中,他们人生的意义也全部系于她,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由她所创造的。
人终究是一种孤独困惑的生物,如果没有引导,他们都不知道要怎样活,实际上,尽管帝国给帝国人民安排了接受教育、分配工作等一系列完整的人生流程,但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活、终日浑浑噩噩的人依旧不在少数。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在领悟自己生存的意义,茫然与不知所措是他们必经的心灵体验,很多人恐怕终其一生也不能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,于是在死前发出人生不过一场大梦的感叹。
他们只是存在过,而不是活过。
而作为她的造物,他们要比凡人幸运很多,因为他们是怀抱着意义而降生的,从她的手中诞生的那一刻,他们就开始活,不必困惑迷茫自己究竟为何而活。
她在创造他们时,已在心中构想过他们的用途。
他们为何而生、为何而战。
他们最终将归于何处。
她在开始创造前就已经设计好了。
他们的诞生并非偶然,而是必然,他们是她意志的延伸。
想到这里,西奥多感到一种深沉的安宁。
生来就有意义,这是何其有幸。
而他又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幸。
因为他能亲眼见到、服侍、触摸他的创造者。能和她同床共枕让西奥多内心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受,他现在十分的幸福,以至于他无法入睡。
一股厚重的暖流,沉甸甸的充盈在他的胸腔,又轻柔的包裹着他的心脏,叫他忍不住想要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。
他用自己的目光抚摸着自己的造物主。
即使合上眼,把那澄澈透亮的眼睛蒙住,她也极为美丽,她的眉眼、鼻子、嘴唇,乃至脸颊、耳朵,和寻常的美人究竟有何区别?
如果要细究这个问题,西奥多也回答不出来,因为他觉得那没有区别。
世界上的美都大同小异。
他只感觉她的身躯要更加精细,任何人和她站到一起都会显得粗陋,让人心生自己很笨拙的感觉,就像他现在即使睡不着也不敢轻易动弹,因为他觉得那很冒犯,在她身边,自己已处处多余,动来动去又显得愚笨。
但他还是可以动一动眼睛的,他满怀崇敬与感动的看着她的睡颜,渐渐的他又想起了一些美学史上的经验。
雕塑家在制作雕塑时为了追求美,是会刻意偏离现实的,就像古希腊的塑像追求着黄金分割,而非真实人体的比例。
哥特式的宗教雕塑通常会把人体拉长,让人显得纤细而不食人间烟火。
为了表达一种神圣永恒的完美之美,进行创作时是可以进行艺术加工的。
但人作为一种男女结合的产物,他的相貌由基因控制又充满了随机性,仅仅保证生出一个美人就已经很是困难,更别提在美的基础上进行超脱现实的加工了。
而她……
她就像经历了艺术加工后的理想化女体,为了展现丰饶和超凡美丽而诞生的雕塑,让人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神之手的存在,她的身躯一定出自神的手笔,因为他很难想象宇宙里能有一对男女能生出这样的她。而她的气息又和巴洛克艺术家贝尼尼的杰作有些类似,美却缺乏情感,精致却极其冷淡,栩栩如生间透出虚无的死意,雕塑她的恐怕是位技艺精湛却缺乏人性的神。
这样的美丽,似乎隐藏一种命运惨淡的暗示,生的欲念和死的遐想如果斗争的太厉害,是会破碎的。
但这种美丽往往也只有在毁灭的瞬间,才能达成绝对的意义。
在他崇拜与哀怜的目光下,她无暇细致的身躯轻轻抖动起来,她把双腿夹紧蜷缩到胸前,在这空间不大的木床上,她的膝盖紧紧抵着他的胯部,她的头也向下垂去,蹙起两道秀气的眉,美丽的脸上露出难过的表情。
是做噩梦了吗?
西奥多担忧地碰了碰她的身体,她的皮肤竟很烫,她张开嘴发出黏稠甜美的喘息,像一个发烧的病人。
“国母?”他轻轻呼唤。
像是听到他的声音,她半睁开一只眼,但那眼神是迷离涣散的,显然她并没有清醒,只是处在朦胧中,在迷幻中追寻着他的呼唤睁开了眼。
在月华如水的夜,她失神的目光让他格外心动。
“怎么了?身体不舒服吗?”他继续询问。
她的腿抖了抖,恍恍惚惚地说:“我尿尿了。”
西奥多有些惊讶,她竟然像小孩子那样尿湿床了吗?她已经愈发像一个幼小的女神了。
“好难过。”
“没关系,只是尿床而已。”
西奥多觉得这样的她其实很可爱,很需要他的照顾。
“我给你换下衣服吧。”
他坐起来用手摸了摸她臀下的位置,很干燥。
她的睡衣也没有湿掉的痕迹。
“……失礼了。”
他分开她的双腿,将她的裤子脱下。虽然是自顾自的跑来隐居了没错,但是她还知道要给自己带几件舒适的内衣,他看着她身上穿的很现代化的内裤,轻轻笑了。虽然床和睡衣都没有湿,但内裤的确是被尿液浸湿了,中心的位置颜色显得更深,散发着潮意……还有一股女性馥郁的香气,以及淡淡的甜腥。
他用手指碰了碰那块湿掉的部分。
这味道他很早就嗅到了,不过那时他以为是飘荡在四周的花香,结果这味道是她发出来的吗?
他完全不怀疑她的尿液可能是甜丝丝的。
他脱下她湿透的内裤,内裤上的污渍和她的阴部有些黏连,他这才意识到让她的内裤湿掉的似乎不是尿液。
他拿着她的内裤,盯着中央的污渍,粘在上面的是湿哒哒像蛋清一样透明黏稠的液体,而且有着很浓重的属于她的气息,这气息让他的身体有些燥热,让他从未有过反应的下体有抽动亢奋的感觉。
他低头看向她光裸的下体,那里还有些湿湿的,而且长得和他截然不同,水液就是从她那粉色的缝隙里流出来,他用她已经脏掉的内裤给她擦了擦那里,她踢着腿挣扎,于是他轻轻握住她的脚踝,让她安分。
但他越是擦这里,她流出来液体的就越多,她像一颗受了伤的果实,不停的流淌香甜的蜜汁,他起身用毛毯给她包了个尿不湿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疯狂不是精神病人的特权,实际上许多正常人也有发疯的可能,过度敏感的内心,对某一事物过度的偏执,都有可能造成疯狂的诞生。
疯狂究竟是人被逼到理智的极点而迸发出的无可奈何的疾病,还是一种面对人生的绝望索性自我毁灭以对抗现实荒谬的选择?
对阿洛而言,这两者皆有,不仅如此,疯狂还是他清醒又不可阻挡的宿命。
他用十分理智的头脑接受了自己是个疯子的现实。
他预见未来的诅咒,在永恒的黑暗中飘荡着,对即将发生的背叛、屠杀与自身毁灭的认知,他那所谓的正义感,只能在被预言的幻象反复折磨的状态下坚守。
而经过长期的离群索居、孤独、仇恨和肆意的惩戒屠杀,还有他本人其实是个未曾接受过人的教育的文盲的情况下,他便再也无法依照她期望的方向成长了。
长期的痛苦让他的思想永久的扭曲,他的头脑混合着恐惧与暴行,那些区分执法者与罪犯、正义与施虐的界限,已经模糊不清,而他也失去尝试分辨他们的力气。
他们说,这是最好的时代,而他知道,这是最坏的时代。
他们说,这是智慧的年代,而他知道,这是愚蠢的年代。
他们说,这是信仰的时期,而他知道,这是怀疑的时期。
他们说,这是光明的季节,而他知道,这是黑暗的季节。
他们说,这是希望之春,而他知道,这是失望之冬。
他们说,人们面前应有尽有,而他知道,人们面前一无所有。
他们说,人们正在直升天堂,而他知道,人们正在直坠地狱。
他早已失去了对她能实现长久幸福统治的安全感,因为预言总是在向他展示未来的恐怖图景,面对那恐怖图景,人类必须放弃他们的人道主义,彼时善与恶不再是衡量的尺度,正义自然而然也会失去意义。
既然帝国势必要不可避免的坠入疯狂的深渊,所有圣人、善人、好人都会变成伪人、恶人、坏人,那么他也不必克制自己残忍的本性,与自己的邪恶基因作抗衡,疯狂只是提前降临在了他的身上。
尽管他还效忠于她,但已经无可挽回的失去了作为她的审判者的资格。所以第八军团继续征战、屠杀、收复,但已经毫无荣誉、骄傲与崇高。
到现在为止,第八军团的疯狂似乎只是自我堕落与毁灭的选择,是用以逃避黑暗的未来的手段,既然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,那么这份疯狂本不该给他们带来太多痛苦。
但是他们毕竟是作为她的审判者而诞生,在她的所有子嗣中,没有谁能比第八军团更迷恋正义感,堕落的人最清楚自己堕落到了何种地步。
自己不过是可憎的屠夫,而非正义的审判官,这种对于自身灾难性本质的认识如此令人心碎,清醒的疯狂最为痛苦,疯狂中的刹那清醒最为绝望。
不是常有精神病人发狂杀了人后,却突然清醒过来,看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内心无法接受进而更加崩溃的吗?尽管他们在此之前乃至于杀人的时候毫无人性、只有疯狂,但行完恶后,良知却降临,叫他们深受道德的折磨。
第八军团就是这样一群复杂的疯子。
他想成为一个正义的疯子,坚信自己的道路,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疑虑,决绝的执行着他的必要之恶。
或者成为一个邪恶的疯子,同样坚信自己的道路,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疑虑,决绝的执行着他的虐杀折磨。
然而事实却是他卡在两者之间不上不下,但凡体验过这种感受的人,都没有办法不去憎恨自己的造物主!
阿洛站在午夜降临号的王座厅里,他的面容是无可挑剔的俊美,但他很瘦削,因此颧骨的轮廓明显,下巴很尖,苍白阴郁的脸因为长期的自我折磨透出一种沉重的神经质。黑色的长发无拘束的洒下,遮住他的额头和部分脸颊,黑而深邃的眼睛没有任何光泽,他身上有一种非理性的、动荡的、毁灭性的气质。
他拿起一把线条优美的刀放在眼前凝视着。
良知、道德、本心……
他一直对这些词心生厌恶,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,但他还有着些正义感的心告诉他这些东西的确存在。
他也很讨厌太阳,看见太阳就像有箭刺进他的眼睛,但他深深痴迷着一颗清冷的太阳。
他不喜欢月亮和星星,那些夜晚太阳的走狗和离他遥远些的的太阳,但他很希望自己能是人群中闪耀的一颗星。
唯一让他安心的只有黑暗。
绝绝对对的黑暗才能包容这样矛盾而复杂的他。
因为那黑暗实在太黑了,所以他大可以想象在黑暗中其实藏着一个光明璀璨的王国,用以给他这样的人生存。
他走到他的受害者面前,刺下了一刀。
他很熟悉刀刃切入皮肤时的那种黏腻的阻碍感。
他先切入喉管,用刀尖一点点碾碎软骨,碎裂的骨渣混合着粉红色声带组织从切口涌出。
男人张大的口腔里喷出血沫。
当刀刃触到他的颈椎时,阿洛在那里反复拖锯,暗红的血液顺着刀身汩流淌,这个时候男人已经死了,他再也不会痛苦了,但他的工作还没有结束。
他继续切割男人已经死去的身体。
软骨碎裂是轻微的嘟嘟声。
肌腱断开是粘稠的噗噗声。
骨骼被锯断则是粗糙的咯咯声。
最后是五脏六腑和着血液滑溜溜滚出肚子的哗哗声。
这些声音听起来才是真正的悦耳。
虽然男人已经死了,但动脉血还是如喷泉般激射,溅到他苍白的脸上,然后让他像流下血泪一样滴落。
他俊美而阴冷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双眼中只有沉迷于此的专注。
当整条脊柱连同胸腔被完整剥离,那上半身失去支撑的肉块倒下坠入血泊。
阿洛捧着他的胸腔,放下刀,伸出手指将他的肋骨一个个向后掰开、展平。手指与湿漉漉的肋骨进行摩擦时,那种感觉带给他痉挛般的快感,他的确从这种折磨中得到了快乐。
他将手中的骨架平铺在地上,那长长的脊柱像是蝴蝶的身子,完全伸展开的肋骨则是蝴蝶的翅膀,这很美丽,非常美丽。
这是人类的“羊蝎子”。
阿洛将它虔诚的放到一边,走向自己的下一个受害者。
这个受害者也是一个男人。
他的刀也是放在了他的脊柱上,但他这次并不是想取出男人的胸腔和脊柱,他想要的是他的皮肤。
阿洛的手划下去。
刀尖也划了下去。
男人白色的肌肤上瞬间出现一条红线,刚开始这道红线很细微,他的肉体还不知道自己被割开了,不过很快,鲜血就像在雪地里晕染一样,细细密密的冒出来,然后越扩越大,越扩越大。
皮肉分离了,就像被割开的真皮沙发的表面。
现在这个男人才发出凄厉又痛苦的惨叫。
他的刀尖再次贴上他的伤口,他横着拿刀,顺着伤口将刀刃斜插进男人的肉体,他像是削一个苹果,让刀刃在男人的表面皮肤和内部血肉间滑行。
这时候男人的叫声已经近乎恐怖。
而他则轻声细语的提醒他要安静。
他很耐心,刀锋过处,皮肤与肌肉依依不舍的分离,他抚摸着这张逐渐剥离的皮囊,等他将它完整取下时,渗着血变成粉红色的男人也已经没有了声响。
阿洛捧着这面人皮,再拿起他之前剥下的骨骼,缓缓的走向王座厅的王座。
王座上坐着一个人。
他用许多人类的血肉像堆雪人那样堆起的人。
这是一个血人,也是一个肉人。
这是他为他敬爱的母亲建立的塑像。
不过比起“建立”,“捏造”这个词要更合适,组成她的肉,都是他一块块割下,再放进嘴里嚼烂成泥后捏出来的。
王座厅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,混合着肉体腐败的臭气,她静默的坐在王座之上,没有面孔,没有具体的形态,只有一个大致的臃肿的人形轮廓。
“母亲,你一定冷了吧。”他把那张人皮披在她的身上。
“我还给你带来了头饰。”他将那由人类脊柱和胸腔制成的蝴蝶戴在她的头上。
“啊,多漂亮~”他半跪在她的面前,他苍白的脸颊上透出不自然的潮红。
如果他会写诗,他一定会像浪漫主义的诗人那样,为她不停地写温柔的诗句,告诉她,她有多么甜美可爱,而他又有多么混乱忧郁。
但他对文学的理解是在有限。
而那在他眼中甜美可爱的塑像,实则看起来怪诞丑陋,由罪人的血肉拼凑而成的她一定也是罪孽深重的吧,就像他一样。
看着这尊由他亲手创造、代表着他恨与爱之根源的女神,他的眼神里没有了方才行刑时的沉迷与专注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孩童般的迷茫与渴求。
血泪早已干涸,在他苍白英俊的脸上留下暗红的痕迹。
“母亲……”
他的声音异常干涩,他顿了顿,期待她的回应,然而,大厅里只有死寂。
如果用天平秤量他对她的爱与恨,那么他对她的爱一定远远的大于他对她的恨。
他恨她将他塑造成这样,既扭曲又破碎。
但孩子爱母亲却是一种本能。
母亲也许不爱她的孩子,但孩子怎能不依赖她?
“没能变成你所期望的样子我很抱歉。”
“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……”
阿洛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,说一位母亲从小溺爱她的儿子,无论他做了怎样的坏事,她都不责怪他,哪怕他杀了人,她也心疼她的儿子,而她的儿子却利用她的爱,在她拥抱安慰他的时候,咬掉了她的耳朵,痛斥她正是因为她的溺爱,他才变成了杀人犯。
真是不知好歹的儿子,有这样的爱不该感恩吗?
只要有爱,就足以相濡以沫。
他伸出手抚摸着她身上那些黏腻的血肉。
“母亲,我好爱你~”
他喘息着低下头去,迷恋的守卫在她身前。
“我好爱你……”他一遍遍重复这得到不到应答的话语。
在这昏暗血腥的王座厅,对着他所爱所恨的母亲深情告白,想必也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吧,如果她真的在,也会被吓跑的。
“我也很爱你。”
耳边竟突然响起她的声音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
发送任意内容至邮箱po18de@gmail.com获取最新访问地址